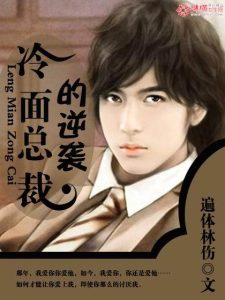一個是沉默的面無表情,一個是無奈到面無表情。
兩人對視了下,陳新說:“瀾小姐。”剛剛我們在這裏你怎麽不出聲叫一聲。
何零兒知道他在想什麽,只不過她在這裏站了一晚上,渾身酸痛到想蹲都蹲不下去,而且外面那麽多人,她是真沒臉叫出口,更何況,她叫了,只不過聲音虛弱,外面又人多口雜,叫了幾聲都沒聽到,聽到外面拿了手電筒了,她也就省點力氣了。
“你為什麽會在這裏面。”
何零兒累到說不出話,但陳新也沒指望她現在回他,派了人去通知了秦禮道,然後退後了一步看這條小過道。
沒過多久秦旻則就趕來了,他見到這情形也愣了下,“零兒?”
何零兒從鼻子裏發出了個嗯,有氣無力的。
“你別說話,保存體力,我這就想辦法救你出來。”秦旻則也像陳新一樣退後了一步。左右兩棟房子,一棟是小洋房,一棟是小平房,一些瓦片堆在地上,瓦片上蓋着雨布。
這裏離東現家也就十幾米的距離,離街區還有一些路,平常少有人路過,他只是左右看了看,就得出了結論:“把這棟牆輕輕的敲開。”
卡的太死,再卡下去,人就會受傷,等不得了。
一聲令下,他們挑了比較好敲的平房那邊動手了,秦旻則伸手進去握着何零兒的手,一邊讓他們輕着點,一邊又安慰零兒。
何零兒懷疑她兩邊胳膊都已經青了,一敲牆,再輕也會帶來一陣不小的顫動,她咬牙忍住。
一晚上的折磨終于看到了曙光,她手指摳着秦旻則的掌心,眼眶酸酸的,嘴巴動了動。
“再忍忍,”秦旻則心疼,“快了。”
“嗯。”一個字他都聽出了滿腹的委屈。
給了平房家一些補償,牆在敲開了一個口子後,被他們一點一點的拿手剝下來了,幸好,為了節約成本,牆體并沒有很厚,何零兒只覺得身體外面的陽光全部照了進來,她被刺的眼閉了閉,人一松,整個人控制不住的往下滑。
秦旻則擠進去接住了她。
她兩邊的衣服都已經磨破了,臉上的傷也因為一晚上的發酵沒有處理而發紅發腫了。
秦旻則橫抱起人,轉身就鑽進車裏:“去醫院。”
***
袖子被剪下,兩邊胳膊都破了皮,再一晚上被壓着,血液不流通,有些發紫了。
秦旻則抿着唇,周身發寒,一聲不吭。
配了些藥,包了傷口,醫生就打發了人走。秦旻則讓陳新去取藥,自己帶人去車上。
兩人沉默了一會,然後秦旻則嘆了一聲氣,手擰着眉心:“零兒你什麽時候回來的?”
“昨晚一出那道門我就回來了。”
“然後就遇上那幾個流氓了?”
“嗯。”
秦旻則靠坐在座椅上,他只要一想起自己在家睡的渾然不覺時,她正被卡的動彈不得,就恨不得回到昨晚把睡覺的自己拉起來。
何零兒戳戳他的手臂:“你幹嘛呀,我這樣又不是你的錯。”
秦旻則拉着她的手把人抱在懷裏,又不敢抱的太緊,以免碰到她傷口。
小心翼翼又珍而重之。
“我昨晚一會想着要自己出來跟着你,一會想着是不是要派些人跟着你,可是,你走的時候是嚴瀾,我覺得嚴瀾的命運,我即使跟着也沒用,如果你是零兒,總會來找我。是我想錯了,不管你是誰,我總該看着你的。”
他摸了摸她的臉,這傷雖然是打在嚴瀾的身上,但零兒回來的時候也會跟着她,跟着一起痛。
他眼裏的柔情太甚,心疼太滿,何零兒不自覺的湊上去對着他的嘴撮了一下。
秦旻則一僵,臉上先是錯愣,後是不知該怎麽表達的喜悅,想揚唇卻覺得眼下這情境似乎不是高興的時候,這一上一下的,他的表情生生的被分割成了好幾部分。
有點傻。
何零兒沒忍住,噗哧一聲笑。
兩人對視,零兒的笑眼非常漂亮,一笑就會彎成月牙兒,裏面盛滿了星星點點的光。
兩人都笑了起來。
笑着笑着,何零兒的頭上蓋住了一層陰影,秦旻則扣着她的腦袋親了下來。
這是一場久違的令他靈魂都興奮到開始顫/抖的口勿。
起先惦記着她臉上的傷,他還刻意放慢了自己的動作,溫柔的舌忝 舌氏,到後來,他就無法控制自己了,氣息也重了起來,最後他略為狼狽的放開了她,轉了頭在車窗上吹風平複自己。
但是仍然捏着她的手放在大腿上手柔手差。
“抱歉。”秦旻則沙啞道。失控了。
何零兒臉紅紅的,“這有什麽可抱歉的呀,一時情難自己過火了點,不是挺正常的嘛。”
秦旻則低笑了聲,身體的燥熱也散的七七八八,回頭捏了捏她完好的半邊臉:“小姑娘說話,注意着點。”
何零兒撇嘴,仰着頭看他,眼睛濕漉漉的:“那你這大男人還想和小姑娘做一些不太想注意的事呢。你可別說你不想哦。”
秦旻則啞然,到底是笑了一聲,沒回話。
兩人又溫存了會,何零兒說:“除了胳膊上的傷是我自己的原因,其他的傷都是嚴瀾的,你別擔心,回去後自然就沒有了。”
秦旻則嗯了一聲,把玩着她的手指,像是玩着奇珍異寶:“她是想讓我們親眼看着她所有的遭遇,我們能配合最好,不能配合她便讓我們暫時消失,讓本體出來繼續。你昨天說戲臺上的你有一瞬間是脫離了她的掌控是嗎?”
何零兒點點頭。
“對呀,所以她還是有漏洞的,但昨晚上她自己就修補了這個漏洞。不過,她也是要先和我們對抗一番才能成功的,我本想着昨晚她再出現的時候我不和她聊天,也不看她要給我做什麽事了,我直接抓了她不就行了?我何必磨磨唧唧的在這裏讓她給我們講故事呢,她想講,我還不想聽呢。”
秦旻則:“……”
何零兒在車裏看着他,見他沒說話,橫眉道:“我說的不對嗎?!”
語氣裏雖說有些嬌蠻,但秦旻則聽在耳裏覺得異常可愛,非常受用。
那種她是自己的女朋友的,是自己獨有的,可以讓自己随時抓在懷裏親熱的舒暢感,讓秦旻則整個人都熱熱的。
非常想去做個極其困難的手術纾解一下。
他又低頭在她唇上撮了一下:“你說的對。”
“但是難就難在她不出來可怎麽辦?如果她知道了我的心思,不出現在我面前了,我豈不是要一直跟着她的步調走嗎?”
秦旻則理着她的長發,她成為嚴瀾,唯一變的就是這頭長發,她從來沒有養過長發,極其不習慣只要随便動一動,就要理一把頭發的事情,秦旻則用手指幫她理順,再揪着一把玩在手心。
“我覺得……她不出來,我們就引她出來。”秦旻則猜測,“你說你在竭力不受她控制,想要掙脫她的時候她出現過聲音是不是?那出現了聲音,她人在哪呢?”
何零兒皺眉思索。
當時太亂了,她扇了西門關一巴掌,臺下一片嘩然,耳邊就出現了聲音,她只怔然在她被侵犯和掙脫成功的雙重心理裏,但…….
她仔細回想了下。
這聲音……
是從她後腦勺傳來的。
對有些道行高深的鬼來說,聲音和身體确實可以分開,但嚴瀾當時,正處于被她脫離成功,被擠出身體最脆弱的時候,這種情況下,她急于想讓何零兒穩定下來,不再讓身體反抗她,她的聲音和身體絕對是無法分開的。
她思考的太認真,以至于沒有發現,秦旻則正在低頭解着她的衣服帶子。
“……”流氓啊。
何零兒拍了一把正在帶子上的手,氣道:“你幹嘛呢?”
秦旻則淡定的說:“想出什麽來了嗎?”
“……”何零兒瞪了一眼他,把衣服從他手裏拉了出來在他面前打了個死扣,然後把他還想捏她手的大手掌拍開。
秦旻則低笑了一聲,傾身抱住她嬌小的身軀:“零兒你得理解理解我。我一把年紀了還不會解小姑娘衣服,說出去讓人笑話。”
“你想把這事說給誰聽?”
“……”當然沒有,只是想在她這博點同情。
“那你要解也不是解這個衣服呀。”何零兒說:“我回去後這衣服也不會跟着我一起回去。”說了一半,她想起什麽,輕擰起眉頭,從他懷裏擡頭看他,手指戳着他,有些指控意味:“還是說,你對衣服方面有特殊的癖好?制服癖?古裝癖?你好變态哦。”
秦旻則氣笑了。
他誠懇的說:“瞎說,我沒有那些癖好。”
何零兒松了一口氣:“那還好哦,我告訴你啊,你要有那些癖好,我可不能老穿,我捉鬼沒那麽多時間買衣服的。”
秦旻則愣了愣,再也沒忍住的手捂着眼睛笑了起來。
她還是那個何零兒,即使中間被他弄丢過三年,她還是那個義無反顧,敢愛敢恨,從不扭扭捏捏的小姑娘。
他真的慶幸時間在他們這兒,像是停滞在過去,也像是平緩的把相同的他們從過去帶到了現在。